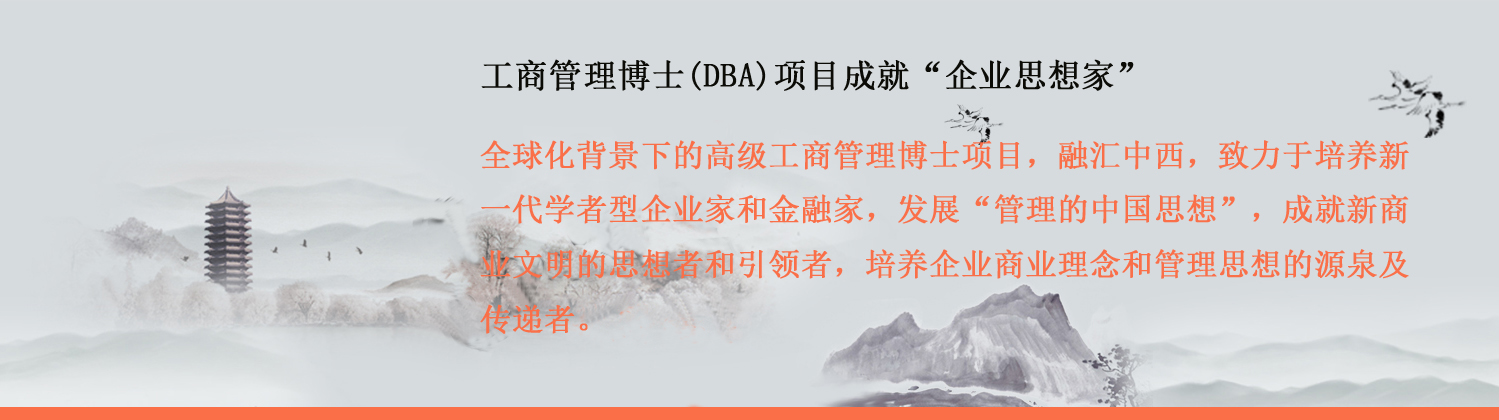导论
1.1 实践与学科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律制定了却没有得到执行?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对这一问题有着持久的兴趣。但更耐人寻味、在哲学上更棘手的,其实是上述问题的反面。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法律如此有效?为什么这些法律能够由国家的工作人员加以执行,而且得到了公民的遵守?毕竟,法律只不过是纸上的一些文字而已。一旦有人停下来认真思考,他不免会困惑:为什么只是一些“纸上的墨迹”,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为什么新颁布的限速法规就能迫使司机开得更慢,而且如果有少数人不这样做,就会有交通管理人员追在他们后面并开出罚单?
传统的法和经济学通过回避来处理上述问题。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直面“纸上的墨迹如何引发行动”这个难题,在接下来的各章中,我将阐述并解释上述谜题,然后试图给出一个解决方法。这会使我们因之质疑并拒绝标准的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法和经济学方法。这种新方法以博弈论为根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以下问题的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法律能够有效?为什么又有这么多法律未能实施,被束之高阁?鉴于法和经济学对于一系列实际领域的重要性,例如从竞争和合谋、贸易和交换、劳动和监管,再到气候变化和冲突管理,正确展开分析的好处是巨大的。在职博士本书将有助于探索横跨经济学和法学的关键领域,对于理解发展与和平、停滞与冲突都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缘地带往往少人问津。尽管有些鼓励实践的不同宣言,但跨学科的研究仍然不多,因为它往往受到已有方法和意识形态差异以及一些固执己见的阻碍,而不易成功。
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法学与经济学的融合显得格外突出。自20世纪60年代该研究领域形成以来,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日益显示出对彼此存在甚至互相需要的认识,法和经济学这个学科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对这一领域的需求是如此明显和巨大,它不应受阻于跨学科研究面临的一般性障碍。法律一直在不断地被制定和执行,一个人不必是经济学家或法学家,也会发现拙劣设计的法律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停滞不前,而精心设计的法律则可以推动经济活动迅猛发展。由于上述原因,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甚至在这个学科有正式名称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活跃的互动领域。例如在美国,对商业集团合谋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9 世纪末。1890 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案》、1914 年的《克莱顿反垄断法案》以及1936 年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案》,均成了运用法律来规范市场竞争和防止合谋行为的里程碑。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实践先于理论。虽然当时还没有法和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发现了一些小的原则,并据此采取了行动。例如,美国的立法者和政治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虽然遏制企业的合谋对国内的消费者有利,但阻碍了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发展。在与其他国家的生产商竞争并向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出售产品时,让本国的公司可以合谋、固定价格或者采取一些违反国内市场反垄断保护的其他做法,可能是更为有利的。这就导致了1918年《韦伯-波莫雷内法案》的出台,根据该法案,只要企业能够证明其大部分产品是销往国外的,就可以豁免不得合谋的法律条款。后来日本从中借鉴经验,在制定反垄断法时也对其从事出口的卡特尔企业豁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让法律的市场影响力得以体现的标志性事件,是盟军在日本二战战败后不久,迅速对其实施了一项精心设计的反垄断法,即通常所称的1947年《反垄断法》。日本后来对该法进行了修订,以重振本国企业。
虽然不像美国的经验那样直接,但法和经济学的实践对日常生活的重要影响,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人类在学会书写后不久就开始制定法律了。最著名的早期法律铭文是《汉谟拉比法典》,这些法律用巴比伦的阿卡德语写就,在第六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逝于公元前1750年)统治期间制定,并刻于石头之上。法典中的某些理念一直延续至今,例如证据的重要性和被告的权利。它还教给了我们一些流行的复仇准则,最著名的是“以眼还眼”。这些法律准则存续了下来,但并非没有争议。在近四千年后,据信是甘地这样警告我们:“以眼还眼,会造成世界的失明。”
事实上,甚至在人类发明书写之前,法律的概念就可能已经存在了,它采取的是口口相传的惯例形式。有人认为,从广义上讲法律先于人类[参见Hadfeld( 2016)的讨论],实验表明,卷尾猴也有公平观念,甚至有惩罚不公平参与者的倾向。然而在本书中,我将避免使用如此广泛、无所不包的法律概念。
法律的起源、什么是法律以及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等问题,一直为人们争论不休。上述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又都围绕着支持或反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巨大争议而引发(参见 Kelsen,1945;Hart,1961;Raz,1980),它们主要是为了回应奥斯丁在1832 年提出的命题(Austin,1832),他认为“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中,如果某一法律规定能够恰当地反映这个社会中拥有最高统治权的某些人或某些群体的已有命令,那么该法律规定就是合理的”。奥斯丁把最高统治权定义为:“这些人或这些群体的命令通常得到习惯性地服从,与此同时他们却不习惯服从其他任何人”(Dworkin,1986,第33页)。但是,为什么这些命令能够得到服从呢?拥有了最高统治权的人和群体又怎样才能避免服从其他人呢(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奥斯丁以及后来的法学家和哲学家都未能很好地解答这些问题。
虽然奥斯丁和哈特都是法律实证主义者,但哈特认为法律是“规则”,这有别于奥斯丁关于法律是“命令”的观点。“法律是规则”意味着并不需要一个最高权力拥有者或更高的权力机构来执法,有一种义务要素自然内生于法律。在这种观点下,法律的概念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公平感。
出于本书的目的,没有必要对法律下一个正式的定义(并且无论如何,这样的定义也不存在) 。通常的情况是,即使没有对一个学科进行正式定义,我们仍有可能探讨并进一步发展它,这里也是如此。只需要指出以下内容就足够了:法律由社会中关于合法行为的规则组成,一个守法的社会或一个法治的社会是一个所有社会成员都遵守法律的社会。我并不假定法律天生具有公平和正义的特性。在我的论述中,既可能存在高贵和公正的法律,也可能存在不公平和压制的法律。事实上,我希望本书能表明一些早期的辩论和争论是不必要的。一旦发展出以博弈论为基础的法律研究的新方法,我们就会看到,一些辩论很难站住脚,因为它们基于的方法论存在缺陷,同时受到了有限词汇量的限制。随着现代博弈论的兴起,我们能够创造出有助于辩论的概念和术语,从而消除由于言语粗糙的论述引发的一些争议。科学进步的很大一部分是基于语法和词汇精度的不断提高,这一点常常未被人们意识到。
新的研究方法将使我们了解一个社会如何变得守法。据称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曾说过(World Bank,2017,第95页):“在建立法治的过程中,最初的五个世纪总是最艰难的。”戈登•布朗的评论通常被视为一个笑话,但其实并不是。它指出了重要的一点,即法律要扎根、法治要盛行,就需要普通民众信仰法律而且相信别人也信仰法律。这种信念(belief)和元信念(meta beliefs)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社会中根深蒂固。上述观点对于本书的主题至关重要。
顺便提及,虽然上面这段话通常被认为是戈登•布朗说的,但似乎并没有他说过上述言论的实际记录,唯一的理由是他并未质疑这一说法。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处于他的境地,有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归于你名下,可能你也不会主动出来澄清。
回到法律起源的问题上,正如我们今天所知,法律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非常具体的形式。雅典的梭伦和斯巴达的吕库古通常被视为“西方法律和政治思想的奠基人”(Hockett,2009,第14页)。梭伦于公元前638 年生于雅典,在城邦陷入混乱时,他成为雅典的执政官。他在创建一个针对所有公民的法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从本书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他致力于那些使经济生活成为可能的法律,这些法律鼓励专业化和交换,并在贸易中采取明确的立场,允许某些商品的交易,又禁止其他商品的交易。它表明不仅国际贸易,甚至连保护主义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与梭伦相对应的是斯巴达的吕库古,他常被视为《斯巴达宪法》的奠基者,提出了有关社会平等乃至财富再分配的理念和规则。当吕库古登上权力宝座时,斯巴达的财富分配极其不平等,据称他因之开始制定规则来平衡土地的占有。除了这些重要的经济规则,吕库古还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法规,例如男性需要在公共场合集体进餐。要想了解吕库古的详细情况,麻烦在于吕库古坚信法律不应被写下来,而是应该作为一种需要被人们遵守的精神准则。这导致了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即许多人质疑吕库古法律的存在,更严重的是,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质疑吕库古本人的存在。
作 者: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